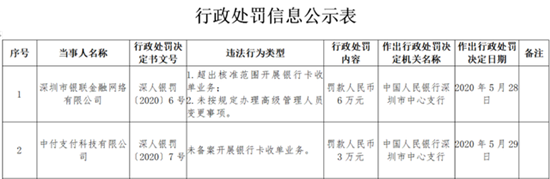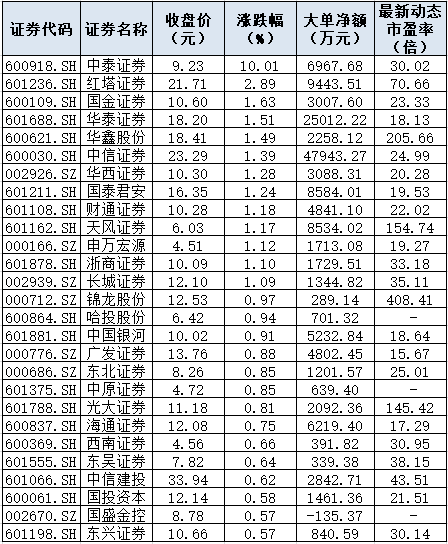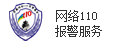草婴原名盛俊峰,当代俄罗斯文学翻译权威,24日晚去世,享年93岁。
草婴原名盛俊峰,当代俄罗斯文学翻译权威,24日晚去世,享年93岁。
尽管大学时听文学社社长朗诵普希金小说《射击》已是37年前,10月24日翻译家草婴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谢谦还是有些惆怅,“傅雷、草婴先生这样体制外以翻译为终身事业的大师,再也没有了。”他觉得,这似乎意味着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时代的结束。
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学优秀译者之一、学者郑体武想到的是,大师凋零,“文学中心主义”也已从日常生活剥离,当代优秀俄罗斯文学介绍到国内的过程更加步履维艰。“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三次热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选择,第二次是国家意识形态起了很大作用,第三次是读者、译者、作者的选择。”和众多出版社一样,郑体武对现状有清醒认识,曾经的盛况可能不会再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都在急剧下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冬妮娅,是八十年代许多年轻人暗恋的对象。图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冬妮娅,是八十年代许多年轻人暗恋的对象。图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
 荣如德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两本书:《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图为1986年上海译文版《白痴》。
荣如德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两本书:《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图为1986年上海译文版《白痴》。
“她那么富有同情心,敢去爱”
“1974年/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谢谦说,学者刘小枫那篇著名的《怀念冬妮娅》1996年在《读书》杂志发表后,他激动不已,想起年少往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谢谦还是大巴山深处一个县城的高中生。家庭出身不好,被降至社会最底层,读大学没有希望……他感到压抑,看不到希望,但是和有些变得自暴自弃的同龄人不一样,谢谦转而阅读文学作品。
那个时代,外国文学作品多来自苏联,《母亲》《铁流》《毁灭》《童年》……谢谦把能找到的书都看完了。幸运的是,县城里还有一批中苏关系交恶前引进的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这也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学、莎士比亚创作之后,公认的世界文学“第三高峰”。这些书在当时是禁书,但总有大胆的人从图书馆偷走。谢谦也暗地从好朋友那里借了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能够与世界一流作家相遇,无疑让狭小的世界突然打开了很大一扇窗口。
尽管毕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令谢谦刻骨铭心的文学作品形象还是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女主角。这位爽朗温和、有着乌黑粗大辫子、喜欢穿一件水兵式衣裙的资产阶级少女,也是当时男孩子集体暗恋的对象。“她那么富有同情心,敢去爱"小流氓"保尔。”谢谦感叹。在宣汉县城,也有一位美丽善良的革命家庭少女,羞涩内向的谢谦却根本不敢跨越阶级差距的鸿沟,吐露对她的丝毫爱恋。
尤其是小说最后,在铁路上铲雪的保尔和新婚后的冬妮娅意外重逢,漫天飞雪中两人对视的细节谢谦至今记忆犹新,就像刘小枫写的,“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而此刻你终于明白/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那时国内作家的"红色经典"都是没有人性、爱情可言,工农兵诗歌中充斥的是红旗、太阳这些意向。读到俄罗斯文学作品,无疑是黑暗中亮起的曙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谢谦还即兴背诵起《致大海》《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给娜塔莎》等普希金诗歌的经典片段,“美丽的夏天衰萎啦,衰萎啦/明朗的日子正飞逝过去……”
“年轻时的阅读,对人一生影响很大的。”特别是禁书中描写的俄罗斯贵族,让他感受到了一种高贵、自由和光明,精神随之提升,这构成了他的性格底色。“我没有沦落,内心也不是那么委顿。”1977年恢复高考后,谢谦如愿考到了北京,是县城里唯一考上大学的青年。 1977年开始,草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作品。图为上海译文1983年版《复活》。
1977年开始,草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作品。图为上海译文1983年版《复活》。

俄罗斯画家伊莉莎白·伯姆(Elisabeth Boehm)在20世纪早期为《战争与和平》的女主角娜塔莎·罗斯托娃所作的插画。
从追随到心态变化
说起冬妮娅,还有当时谢谦为了那惊鸿一瞥的《天鹅湖》片段,而反复观看的革命电影《列宁在十月》,表情严峻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也笑了。他是60后,年少时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没有谢谦深,但那些美好的片段依然是青春期难以磨灭的记忆。郑体武后来选择了俄语专业,并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
“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俄罗斯文学一样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郑体武说。俄罗斯文学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五四”时期。鲁迅翻译了果戈里的《死魂灵》;瞿秋白翻译了《三死》、《伊拉司》、《阿撒哈顿》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巴金更是译著颇丰,翻译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等作品。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俄罗斯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影响最深。在文学观念、题材还有语言革新上影响都非常深远。”郑体武还特别提及,当时西方文学更注重消遣、娱乐,俄罗斯文学则严肃沉郁,这种“为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是晚清以降,以救亡启蒙为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后,最终确定以俄罗斯文学作为学习对象的重要原因。很多作家用白话文写小说也是模仿俄国作家开始,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
1949年至“文革”前,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郑体武说,在国家大力倡导下,大量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当时的文学作品就不太喜欢,其实就是不少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了。但和同时期中国作家相比,苏联作家艾萨克·巴比尔难道显得粗糙吗?”
不过,在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受中国读者欢迎,是有疑问的。“当时政治形势下,被冠以革命色彩的苏联文学实际上是被脸谱化了,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很难去掉。就像智利诗人聂鲁达在中国一度被认为是革命诗人,其实他的情诗写得非常好。”他认为,这也是后来,更多外国文学引入中国后,俄罗斯文学开始流失读者的原因之一。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俄罗斯文学再次繁荣起来。翻译界聚集了大批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俄语人才,草婴和荣如德等老一代翻译家也重新拿起译笔。以草婴为例,1977年开始,他翻译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荣如德则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两部长篇小说《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时郑体武在苏联留学,他记得当年购买一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要凭票,印量达到1700万套。而在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热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译林》发行量空前,为了买到最新的杂志,有人甚至凌晨两三点就在邮局门前排队。
不过,郑体武也说,80年代“老朋友”回来后,国人心态发生了变化,不再唯俄罗斯文学马首是瞻。“这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自然对其他国家文学产生兴趣。又恰逢拉美文学爆炸,展现了一个魔幻而全新的文学世界,对读者吸引力自然更大。”
翻译大师逐渐凋零
在位于上外的办公室里,郑体武的书桌上堆着小山似的书籍,摆在最上面的是新近出版的译作《落叶》和《隐居及其他》,作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重要代表的罗扎诺夫(又译罗赞诺夫)。“封面设计得很美,还分成了上下两册。”他拿起一本《落叶》,摩挲着封面告诉记者。罗扎诺夫被认为是文坛怪才,郑体武一直想在中国推广其作品,但几年下来,读者反应非常平淡。
此前,郑体武还翻译过《勃洛克叶赛宁诗选》,以及最受俄罗斯读者欢迎的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的代表作《夏伯阳与虚空》。这本书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4,但发行量非常小,“只印了5000册,现在想买也买不着。”对于两部呕心沥血的新作将面临何种市场反响,郑体武不愿谈太多,“我翻译不是为稻粱谋。”
如今,郑体武这样的有稳定高校工作的学者,构成了高质量俄罗斯文学译者的主要队伍。“像草婴先生那样做专职翻译,完全不能生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他也想全身心投入文学翻译,但是不得不在生计、职称等现实面前低头,“出版社的翻译稿费,一般千字80元。我曾经花差不多两年业余时间翻译了一本20万字的优秀俄罗斯文学作品,稿费1.6万元。而我的学生出去做商务口译,一小时就可以赚几千元。差距这么大,年轻人也有生活压力,谁还愿意来翻译文学作品?”
何况,就像90年代时,草婴先生等人反对将上海翻译家协会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时坚持的一样,文学翻译是有门槛的。“我们始终认为,翻译者和翻译家是两码事,翻译家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者。”当时,草婴这样说。黎遥也告诉记者,译者的黄金时段是30岁至50岁,但现在俄语翻译两极化特别严重,或者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或者是老先生。年轻人会有行文、翻译方面的错误,一些老先生则思想断档,“曾经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有人会在翻译过程中认为原作者的思想不对,自行修改或者干脆删除。译者怎么能随便介入作品呢?是否删减应该是由专家论证,而非译者的单向处理。”
不管怎样,在译林出版社俄罗斯文学编辑冯一兵看来,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师凋零,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除了刚刚仙逝的草婴先生,4月,他还送走老师、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余一中。而去年底,曾与巴金合作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家臧仲伦先生也逝世了。“看着熟悉的老先生一个个走了,非常难受和遗憾。”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人文情怀依然存在
“俄罗斯文学出版在中国不是热点。包括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半个多月以来,市场反响依然比较平淡。”10月29日,霜降的一场雨后,黎遥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冯一兵也说,如今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集中在名著,诸如俄罗斯布克奖等国内大奖中涌现的优秀现当代文学作品,从90年代开始译林出版社就一直在推,“但是曲高和寡。”
“这可能与读者阅读口味有关,也与地方的整体气息有关,毕竟文学是奢侈品。”黎遥是70后,因为时代原因,幼年时还接触过经典俄罗斯文学作品。但他发现,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读者,对俄罗斯文学就有明显隔阂了:他们会抱怨小说人物名字很长,难记忆。书中展现的俄罗斯生活习惯也非常陌生。“当代中国读者,对日本甚至韩国文化的熟悉程度都远超过俄罗斯。这与文化输出有关,中国观众看日剧、韩剧,甚至泰剧,还有宝莱坞电影,但是对俄罗斯影视作品,还停留在《兵临城下》——那都是十几年前的电影了,我们对当今俄罗斯的叙述方式非常陌生,不管是影视,还是文学作品。”
采访中,译者、读者,还有出版社编辑都一致认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曾经的辉煌很难重现。“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是在无书可读的特定时代形成的。”谢谦强调。郑体武则认为,其实不仅是俄罗斯文学,全世界范围内文学都面临衰退。
多元化选择之下,还应该再读俄罗斯文学吗?“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冯一兵说,苏联解体后,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比较大,写作风格千姿百态。但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包括后来的“白银时代”以来,一代代作家自觉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对普通民众深刻的人文关怀,还有细腻的写作手法,这也是俄罗斯文学闪耀的独特魅力,“你如果看了普拉东诺夫的俄文版小说,会流下眼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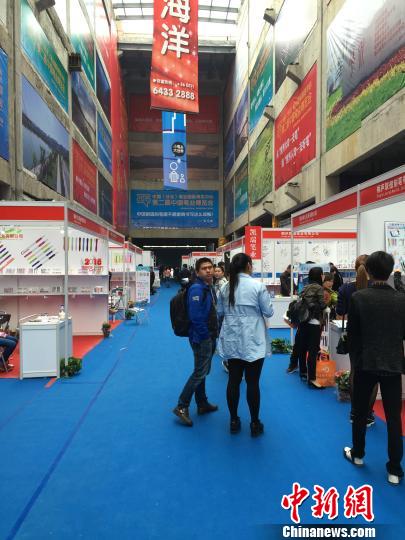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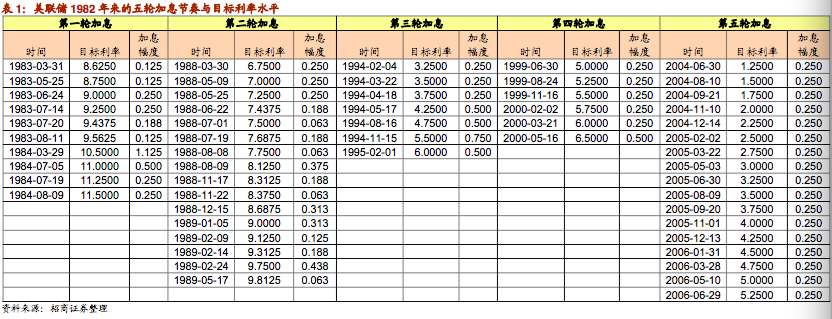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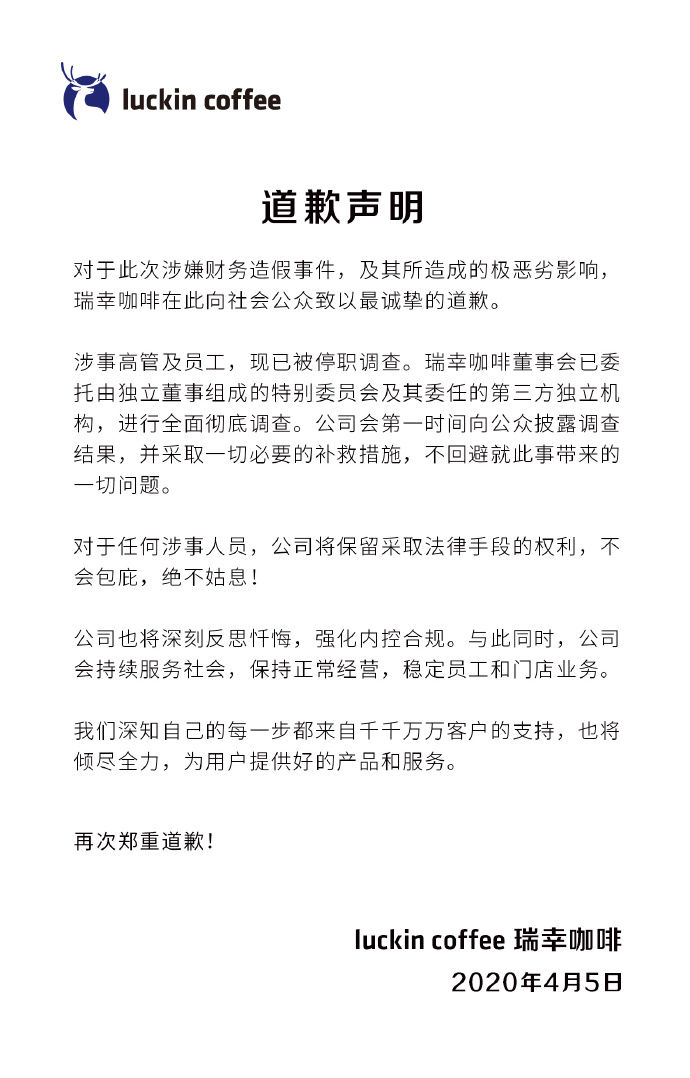 瑞幸咖啡就财务造假事件致歉
瑞幸咖啡就财务造假事件致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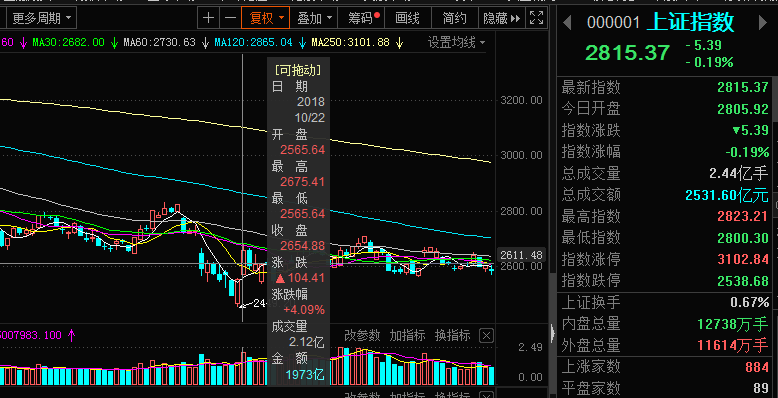 重磅利好出现!金融委再度定
重磅利好出现!金融委再度定
 国产耳机品牌Nank南卡重拳出
国产耳机品牌Nank南卡重拳出
 比特币年内涨幅超过150% 中
比特币年内涨幅超过150% 中
 中兴通讯科技公司将投资146
中兴通讯科技公司将投资146
 宁夏灵武农商银行一董事又“
宁夏灵武农商银行一董事又“
 蜡梅凝香袭人,奈雪的茶推出
蜡梅凝香袭人,奈雪的茶推出
 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
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