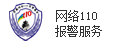12月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律师刘巍算了算,过去12个月里,她接到了5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求助电话。一些人在申请低保的过程中遭遇了隐私暴露,一些人则在患病后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些人的学业即将画上句号。他们都想从刘巍这里寻得走出困局的办法,50多个各不相同的遭遇,但皆因感染艾滋病而起,刘巍尽可能地提供着法理上的支持。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但有一点刘巍可以确定,在一次次言语上的交流过后,这50多名感染者最终没有提起诉讼。做律师20年,帮助感染者维权也已经15个年头,刘巍曾相信,诉诸法律是不变的正途。直到从一段段与艾滋病有关的人生中走进走出,她已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坚持。
缘起
被驳回的艾滋病就医歧视案
2012年10月,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肿瘤医院接受治疗,但在手术前夕被院方告知因携带艾滋病病毒不宜手术,被迫出院。在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更改病历的方式,让晓峰在天津另一家医院成功接受手术。此事被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争议。随后,天津市卫生局表示,经查实,天津肿瘤医院确实存在推诿艾滋病人的情况。2013年2月,晓峰将拒诊的天津肿瘤医院诉至法院。
“晓峰案”被视作我国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诉讼案,这其中的标杆意义不言而喻。
在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将天津肿瘤医院起诉后,晓峰提出了书面道歉和经济精神损失费赔偿两项要求。两项要求自有其中的深意。
“无论道歉还是赔偿,都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判决结果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晓峰说。
虽然,晓峰成功地吸引了舆论注意,却最终没能等到开庭。
作为晓峰案的代理律师,女律师刘巍也被卷入其中。因为这个案子,作为“艾滋公益律师”让她声名鹊起。但让艾滋病人站在法庭上,暴露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维权真能有所裨益么?
在去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时,刘巍过得并不顺心。经历了四次调解,晓峰案件的开庭日期仍然迟迟未定。又过了两周,刘巍终于等来消息,法院驳回了起诉,理由是诉讼请求中的“平等就医权”不在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当中。
2000年,是刘巍初入这个圈子的时间。河北武安的王为军出现在她面前,30多岁的汉子,胡须和头发已经很久没有修剪过。妻子在遭遇违规输血后感染艾滋病去世,2岁女儿的感染者身份也已确定,王为军正用一种蓄发明志的方式,表达着自己起诉医院的决心。
刘巍不恐惧于与感染者的接触,但从法律的角度也并不看好此类维权案件的前景。“取证难,胜负难料,那时律师都不愿意接这类案子。”
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爱之方舟”的负责人孟林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看到,开始有法律界人士介入感染者维权。随着多地“血液污染”的消息爆出,开始有感染者聘请律师。“那更多还是种单向的联系,互助组织和律师直接没有过多的合作。”
同样是在2000年,艾滋病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体现感染人数的示意图上,那条曲线呈现了跳跃的趋势。
境遇
无法归类的感染者
刘巍的名声渐响,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想找到这名律师的联系方式并不是什么难事。过去一年里,刘巍接到了50多个来自感染者的求助电话,所遭遇的问题关乎名誉、生计,又或是学业。
但在孟林成为感染者的上世纪90年代,即使有不公出现,沉默是多数人的选择。
随着一些维权案件的胜诉,更多不同类型的案件开始出现。在刘巍经手的案件中,起先是那些隐私被暴露的人,而后还有因病情遭遇就业不公的人。
遭遇各不相同的感染者中,无论感染途径是什么,都不再成为人们尝试谋求平等权益的阻碍。
到最近一年刘巍接到的这50多个电话,她已经没法再把感染者所面临的问题笼统的归类。
一位感染者尝试着申请低保,却被居委会在公示时暴露了病情;一位感染者被伴侣知晓了病情,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一位感染者是医生,他怀疑自己是在手术时遭遇了“职业暴露”。
但最让刘巍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声音。一年里,三名大学生找到了刘巍,他们都是刚刚确诊,担心被校方知晓后学业就此中断。
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仅2015年前10个月,全国共报告2662例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8%。而以北京为例,近两年每年新增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100多例。
对于这些数字,刘巍有着更真实的感受。或许是因为本就不错的教育背景,找到刘巍的大学生们大多情绪平稳、可以条理清晰地讲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但仔细听着,语气中总是透着种无奈出来。
与感染者接触得多了,刘巍已经知道其中的避讳,除非涉及关键的问题,否则她不会问起对方感染的原因。而那些打来的电话,虽在接通时称谓客气,却也没谁会主动报出自己的姓名、家乡。“一些人会说是在帮别人咨询,但能听出来,他们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每个求助电话的时间也就在半个小时左右,刘巍尽可能搜罗着相关的法条,希望能够提供到切实的帮助。但每个号码挂断之后通常不会再次打来,刘巍也无从得知,电话那头的人们之后的境遇究竟如何。
就刘巍所知,艾滋病感染者一般不愿意选择诉讼,一来要冒着被曝光的风险,二来他们羸弱的身体往往等不到开庭那一天。
勇士
愿意站出来的人
“爱之方舟”的办公室距离刘巍的律所很近,两栋写字楼隔着几百米的距离遥望。而在律所另一边的不远处,就是佑安医院的所在,众多艾滋病感染者在此确诊、就医。刘巍说这只是种巧合,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也映合了感染者、法律界人士与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位置不同,距离很近。
遇到不平,感染者最愿意寻求的,仍然是“爱之方舟”这类互助组织的支持。在孟林的理解,原本就是同病相怜,一种信赖自然而生。
而面对维权类的求助,孟林提供给感染者的通常是三条道路:互助组织帮助联系律师,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由律师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由受过律师培训的互助组织成员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在介绍的时候,我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倾向性。”
刘巍算了算,在过去一年接到的50多个求助电话中,五分之一的感染者在最初明确表示要诉诸法律。她详细地向这些有意者介绍着为此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在这之后,再没一个人愿意走到公堂之上。
孟林不喜欢这些“变卦”的人,一位四川的感染者被医院拒诊,最初找到“爱之方舟”时,言之凿凿誓将官司打到底。孟林帮他联系了新的医院,治疗完毕,这名感染者却不见了踪影。“他们好像更看中的是互助组织手中的资源,但没有太多人愿意真正的站出来。”
刘巍也曾坚定于对簿公堂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王为军的案子,她几赴河北,庭审上动情得把王为军的女儿比作“天下最可怜的孩子”。对那些诉讼当口退缩的感染者,刘巍也曾不解,甚至责怪。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刘巍理解,像孟林这些感染者互助组织的成员,为何需要有人勇敢“站出来”。一场诉讼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还可能转变人们对一个群体的认知。
可她不敢忘了自己律师的身份,当事人的利益无法被忽视。刘巍回想着这些年接触过的感染者,一些人紧握着法律的利器走到了最后,一些人在中途知难而返。无论结果如何,感染者所背负的“诉讼成本”确比常人重了许多。
感染者维权案件审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料,这些都有一个个例子佐证,承担这一切的,是一具具本就被疾患缠绕的身体。
落幕
她希望走进法庭 为维权来一场激辩
孟林眼中,刘巍这样的法律界人士,在感染者维权领域利用率并不算高。这样的现状可能会持续很久,但仍不能否定他们的不可或缺性。那一天会面结束,孟林在微博上写道:“这些公益人往往远比所帮助对象更加卑微。”
刘巍承认,她已在开始调整感染者维权案件和日常案件的比例,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还有些压力的伴随。律师代理官司,无论胜负本是常态,但涉及感染者的案例,刘巍却很难控制自己的心绪。“那输赢之间,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利益。”
又是一年的12月1日,但刘巍觉得,所谓的艾滋病日并没和她有什么实质的联系。她能确定的是,之后一年,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感染者依然会打来电话。
也许不久之后,她就会再有机会走进法庭,为了维护一些人的权益,来上一场激辩。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汨
更多精彩资讯>>>





 厨电逆势增长成炙手“香饽饽
厨电逆势增长成炙手“香饽饽
 莱索托矿区再挖掘出巨钻 重
莱索托矿区再挖掘出巨钻 重
 京东618城市接力赛活动狂欢
京东618城市接力赛活动狂欢
 比特币年内涨幅超过150% 中
比特币年内涨幅超过150% 中
 中兴通讯科技公司将投资146
中兴通讯科技公司将投资146
 龙虎榜揭示机构鼠年心头好
龙虎榜揭示机构鼠年心头好
 疫情之下的“隔空”情人节:
疫情之下的“隔空”情人节:
 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
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