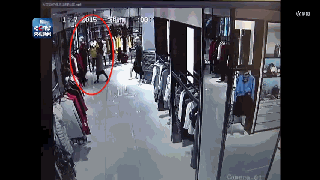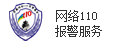学者段九州在《中东研究通讯》上撰文指出,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一系列中东政策来看,美国正在恢复罗斯福所提倡的“51%股份”的设想。如今的美国依然关注中东,依然期望在中东发挥作用,但是面对国内经济复苏压力,美国期望盟友国家更多地分担自己在这一地区的责任。立足回归罗斯福主义的考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坚决反恐的美国对打击ISIS的态度似是而非,曾经豪言促和的美国对巴以问题得过且过,曾经热衷于改造中东社会的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责任避之不及。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是著名美国政治学者、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20世纪70、80年代,当现代化理论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逐渐式微后,国家回归学派和历史制度主义兴起,米格代尔在这个大潮流中进行了调整和反思,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路径,对“国家中心主义”提出了建设性的挑战。
2014年米格代尔教授出版了《流沙:美国在中东》(Shifting Sa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他在该书中回顾了美国自二战以来的中东政策。他认为美国一以贯之的海外策略是,寻找“英国在欧洲”式的本地盟友,分担美国的责任,并与之成立类似北约的安全联盟。小布什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在于其对中东复杂性的错误理解。米格代尔教授最后提出,美国正确的中东政策应该是建立广泛的盟友体系,并推行渐进式的改变,而非利用武力强制推动转型。
罗斯福的全球战略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世界是一家上市公司,美国应该是公司董事局主席,掌握51%的全部股份,允许其他国家共同持有剩余的49%的股份。虽然美国作为世界首要大国的角色始于二战之后。事实上,罗斯福早在二战之中就意识到世界权力格局的转换,并开始思考如何将美国的影响力投射到全球。罗斯福为美国规划了什么样的全球战略呢?
第一,罗斯福认为美国的领导力是全球性的,它必须活跃于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全亚洲。第二,罗斯福相信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帮助建立服务美国利益的理性世界秩序。
第三,罗斯福试图成立世界大国俱乐部,其成员间合作可以保障新国际机构的运作和对付麻烦制造者。这个俱乐部类似1815年为了反对拿破仑而成立的欧洲同盟。在罗斯福看来,美国将是维护世界秩序的首席警察,其他大国是美国的主要战时盟友:英国、苏联和中国。第四,罗斯福放弃了前殖民帝国直接占领海外领土的战略。尽管美国在一度想在战后继续占领菲律宾,但是罗斯福认为,维持海外领土对美国来说有巨大的经济和道德负担,尤其因为美国本身也曾为反殖民宗主国而战。
随着美苏争霸格局在1947年的确立以及1949年国民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时任总统杜鲁门不得不放弃了罗斯福“四个世界警察”的设想,转而与苏联在全球各个区域展开竞争。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北约的成立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投射到各个地区,其中西欧的模式最为成功,即与若干地区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维持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相比美国与英国以及其后的德国建立起的稳固而深入社会的战略关系,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伙伴则从未达到类似的水平。如何将西欧模式复制到世界其他地区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核心。
美国为何重视中东?
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东的评论家提到,“中东已经成为世界的隐喻”。自从二战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关系和美国海外活动的焦点。由于其处在亚非欧三洲交界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中东从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时起就是世界大国的必争之地。在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里,石油的发现促使当时的世界霸主更格外关注中东。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畅销的货物,二战以后,美国意识到石油供应对未来战争的战略作用,爆炸性增长的工业生产同样需要石油,而全世界大约60%的石油都在中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通道的必经之路,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航道关口。在保障能源运输和航道畅通的同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存在,也让美国可以对中亚、南欧、南亚和东非地区的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
除了战略资源和地理位置外,美国的国内的社会团体诉求同样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强大推手。早在19世纪,在宗教驱动下,美国的基督教朝圣者、旅行家(包括马克•吐温)和考古学家(为寻找圣经教义的物理证据)对中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一战后巴勒斯坦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离,美国国内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群体愈发关心陷入冲突的中东局势。
此外,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获胜强化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认同。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代表,强大的美国犹太院外集团,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致力于确保美国奉行亲以政策和中东事务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地位。而美国的福音派(Evangelical)基督教群体,则把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作为天国降临的基本前提,在最近几十年里把其教义预言和美国中东政策的关联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来说,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中东的渗透以及保障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是其核心战略目标。在冷战中,中东的战略地位并非比中欧和东亚更重要,事实上,后者才是美苏对峙的前线。在中欧和东亚地区,大国的实力均势已经形成,武力威胁或者谈判接触都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源于既有的冷战双方互动模式,任何新的政策几乎不可能打破僵局。
而中东地区拥有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部落、宗教、民族、派别林立,地区的联盟和敌对关系也瞬息万变,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是朋友,这为大国在中东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和施展外交手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为例,在1952年革命之初曾获得美国支持,抵挡了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上的军事介入;随后又转投苏联的怀抱,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政策,在对以冲突中获得大量军援;1979年后,埃及再次接受美国的领导权,政治上与以色列媾和,经济上进行自由化市场改革。
二战以后的美国中东战略
尽管美国拥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但是中东地区的波云诡谲还是让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跌宕起伏。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5年,即1945到1970年,美国在中东地区麻烦缠身。曾经被美国刻意扶植的地区盟友埃及和伊拉克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转投苏联。而在罗斯福时代和美国建立盟友关系的沙特,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缺乏对地区的领导力。另外两个非阿拉伯国家盟友,土耳其和伊朗,在这段时间正在追求脱离传统中东文化的进程之中,并不想过多参与中东事务。
这期间的三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对中东事务都没有展现出过高的兴趣,从苏联威胁北约盟国土耳其和从伊朗撤军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到1967年阿以战争,他们对中东的介入更多的是为了抵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这一目的在1957年艾森豪威尔想国会提出关于中东的特别咨文中表露无疑,“由国会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中东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总统有权应这些国家的请求提供武力援助,只要这些国家面临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武装侵略”,该政策史称“艾森豪威尔主义”。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即1970到2001年,美国在这一时期同时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大国埃及保持了盟友关系,达成了诸多战略目标。虽然伊朗国王的倒台和伊斯兰革命是美国盟友体系的挫折,但是这相对也刺激了阿拉伯海湾国家在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形容,“在20世纪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在中东地区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和保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前殖民帝国英法肯定没有,苏联也没有。”
整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后遗症,美国在于苏联对抗中处于守势,因此从尼克松到卡特任期内,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减少与苏联的冲突和赢得阿拉伯大国的支持”。从1972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驱逐17000名苏联专家而逐渐转投美国阵营到1979年埃及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基本达成了上述政策目标。
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改革与新思维”,里根时期的美国的中东政策与苏联对抗的意味逐渐淡化,伊斯兰革命以后的伊朗成为美国眼中的地区新威胁,以至于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苏联盟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在中东地区制衡苏联的战略目标。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中东政策往往被评价为“缺乏长远战略的危机管理”,正如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扮演的保护盟友的“救火队长”的角色。
第三个时期是后“9.11”时代,2001年以后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冒进不仅伤害了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也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全球地位。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使美国的中东盟友阵营急剧扩大,美国也第一次在中东地区永久性驻军,其在中东的地位进入全盛时期。
基于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重新思考,新保守主义思想在小布什政府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在失去共同敌人苏联之后,美国将面临全球多方势力的威胁,包括崛起的中国,反美国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尤其强调“恐怖分子威胁了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在必要时,美国应该同时制衡、打击多个对手”。“9.11”事件的发生似乎证明了新保思想家的预言。
怀着保卫美国利益和重塑后冷战世界秩序的理想,小布什政府先后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试图以此展开全球反恐活动和树立以战后伊拉克为典范的中东民主化蓝图,反恐和民主化成为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的主轴。奥巴马时期的中东政策并非完全背离小布什的政策,他同样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对外输出民主自由价值观。
但是他抛弃了布什政府的两个大胆设想,一是美国能凭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二是美国可以重新建构任何中东国家的内部运行机制。2011年阿拉伯动荡之后的中东变得愈发复杂,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与布什政府的军事介入政策渐行渐远,而更多地采取依靠本地盟友和“离岸制衡”的政策。
结语
半个世纪前,伊拉克裔英国历史学家伊利•克多里(ElieKedourie)曾经警告大国企图控制和改造中东的欲望:“自从19世纪以来,当所谓的改革在奥斯曼帝国推行,没有一个西方大臣和外交官认为中东政治充满希望。我们应该拥有常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东动荡不止,政治强人尝试实行激烈的改革,但从未成功。也许我们应该更谨慎地认为,现代中东的病态不是暂时的,它的政治不稳定更多的是深层次社会和智识危机的结果,改革者的宏图和慈善家的好意都很难缓解和修正它。”克多里一语成谶,21世纪初的美国为尝试改造中东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以失败告终。
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一系列中东政策来看,美国正在恢复罗斯福所提倡的“51%股份”的设想。如今的美国依然关注中东,依然期望在中东发挥作用,但是面对国内经济复苏压力,美国期望盟友国家更多地分担自己在这一地区的责任。立足回归罗斯福主义的考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坚决反恐的美国对打击ISIS的态度似是而非,曾经豪言促和的美国对巴以问题得过且过,曾经热衷于改造中东社会的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责任避之不及。
在11月21日纽约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中东问题演讲中,美国国务卿克里并没有提出解决当前叙利亚、伊拉克和巴以问题的具体战略,而是描绘了一幅“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人民自由通行、男女教育平权、行者免于恐惧”的乌托邦式未来图景。当被问及美国中东政策捉襟见肘的原因时,克里无奈地解释说,“在世界权力多极化的时代,外交决策远比双极体系的冷战时代更为复杂”。现实的确太残酷,或许面对当前泥潭般的中东乱局,就算罗斯福再世,都会嫌“51%股份”太多吧!
参考文献
Joel S.Migdal, Shifting Sa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版权申明本文为中东研究通讯研究团队原创,已授权和讯网智库频道转载。如有意转载或引用请直接与中东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MenaStudies)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