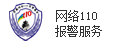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竹杖芒鞋》公众号刊文指出,郑永年近期一篇批判中国知识短缺的文章引起学界热议,但他文章中的一句话似乎容易被忽视掉,但又很重要。他说,“明显过度市场化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也使中国发展缺乏动力。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这句话,似乎点到了中国大转型中的“社会”面向。这就对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很高的期待。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郑永年这位“海外政治学者”这几天因为一篇《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的文章而备受关注,也引起一番讨论。郑的核心观点是,目前中国的改革事业,存在严重的知识不足的现象,尤其是经济学家无法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框架,而是忙于论证政策的合法性。
他重点批评了模糊不清的政策建议,这些成了无法不包的东西,到处都在炒概念,而这些概念要不就被滥用,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外交,都用这些概念,要不就是忽略了一些概念深刻的经济背景。他说: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
这一言论得到了认同,但也遭到了批评。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的文章。他认为“郑永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一,“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能不能得到采纳,完全是由领导说了算。”第二,“实际上,知识分子是对许多政策提出批评的,包括之前的刺激计划”。
这种争辩是有意义的,直接切中了当下中国权力与知识关系或者是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很多地方都值得讨论。但是郑永年说错了吗?他真的是把板子打在了“知识分子”身上了吗?要我,我只能说,“该打,而且打得还不够重”,但是郑的言论很明显不是仅仅在讨论知识分子本身。
所以这中间有两个问题,一是现代性体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按照福柯-鲍曼的视角来看,现代国家从荒野牧羊人的角色转向了园丁的角色,要对疆域内的人口进行微观管理的话,所需要的最关键的知识就是“统计学”,因此,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往往在现代国家中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知识群体。二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迫切需要经济学家提供知识供给。
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自然,经济学家被体制更充分的吸纳,是势所必然。能不能提供新的知识,就不仅仅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结构性位置、学术素养和社会关怀,也取决于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形态。我想郑永年的重点是后者。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一群挨着权力中心的人,在中国又更是如此。所以聂辉华的回应是无力的。但郑永年也并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他只是想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处境的批评来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他只不过是“不点破”而已。
但郑永年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似乎容易被忽视掉,但又很重要。他说,“明显过度市场化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也使中国发展缺乏动力。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这句话,似乎点到了中国大转型中的“社会”面向。这就对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很高的期待。
但是很显然,社会学处本来在社会科学鄙视链的低端,对于强调实务、经济效益、社会稳定的中国来说,地位更是尴尬。因此,90年代至21世纪初,还有许多学者就市场-社会转型过程进行研究,对社会进行诊断,而这些年却在高呼社会学春天的到来,开展各种幸福指数测量、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基层网格化管理、社会管理创新这类“治理术”研究,阉割了自身的“公共性”。
社会学理应是离权力中心最远的学科。对社会学来说,更应当拒绝研究上的“庸俗化”,去捍卫这种公共性。在眼下这个转型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帕森斯,而是更多的米尔斯、布洛维,我们要探讨的应当是市场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 、民众与政体的关系, 我们需要知道权力支配的根源、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个体苦难的社会根源以及如何去生产并保卫社会。
不过,我有一点不敢苟同郑永年的是,他在最后寄希望于中国的智库建设。这一点,估计他要失望了。就在不久前公布的25家国家级智库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几乎网罗了该校所有社会科学学者, 再比如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由张维为挂帅“首席专家”。
因此,知识不会短缺,短缺的是知识分子“断舍离”的勇气和对“公共性”的坚守。

 PPI 45个月负增长 货币宽
PPI 45个月负增长 货币宽
 荷兰首试驾无人迷你巴士 预
荷兰首试驾无人迷你巴士 预
 成都整容乱象:女孩整形填18
成都整容乱象:女孩整形填18
 “明星企业”助阵 深圳高效
“明星企业”助阵 深圳高效
 宝能系一年内或难进万科董事
宝能系一年内或难进万科董事
 已跌破2850点水平的低估值股
已跌破2850点水平的低估值股
 成都飞艇德阳撞高压线爆炸
成都飞艇德阳撞高压线爆炸
 丰田就完购大发与其达成一致
丰田就完购大发与其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