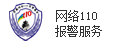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
|
周子章 面临着改革深化的具体落实压力,当前在经济去杠杆化与风险之间呈现了加杠杆与去杠杆的矛盾。修改后的《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硬约束。在中央政府杠杆逐步加大,地方政府杠杆持续压缩的趋势下,未来我国将更多通过改变融资结构的方式来去杠杆,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加大坏账注销来降低负债;而权益上升需放开IPO限制、推行注册制,加快国企改革、增加国资证券化比率,并放开在国企和垄断领域并购融资的限制。
看刚刚公布的8月一系列经济数据,二季度短暂的经济回升态势没能得以延续,有些指标甚至已跌回金融危机深重时的水平。这主要是支撑传统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和外贸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动能不足。我国实体经济总体债务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幅上升,眼下正面临着改革深化的具体落实压力,在经济去杠杆化与风险之间呈现了加杠杆与去杠杆的矛盾。
在经济分析中,人们通常使用债务与GDP之比,来衡量一国债务水平的高低。宏观数据测算结果显示,过去几年,中国总体债务水平显著上升。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目前我国住户、企业和政府等部门的债务仍然可控。住户部门债务负担不高,未来进一步扩张负债的空间也是存在的;企业部门负债水平处于各国区间的偏上端位置,并没有偏高;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去几年增长比较快,地方政府手中持有大量资产,同时中央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相当稳健且中央对地方负有救助责任。
不过,债务偿还的成本也让一些地方政府陷入了困境。沉重的利息负担使得今年经济增长动力反弹的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着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新增GDP与整体债务比率(或叫固定资产的生产率)自2003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从83%降至今年一季度的46%。投资效率降低的情况在2009年之后尤其显著,部分原因在于投资回报突然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的生产率可能持续下滑,这一点特别令人忧虑。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变化在于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技术短期稳定,从要素角度看如果不愿放弃高增长目标,稳增长就只能靠增加资本投入。而2008年危机之后每次稳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实现,体现为投资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全国投资与GDP之比已接近90%。与投资高增速对应的是融资需求始终居高不下,投融资增速始终在15%以上,远高于7%左右GDP增速,因而,货币超增是导致债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而随着全球宽松政策的持续,经济复苏的动力不足,政府过度负债引发的风险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尤其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容易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尽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一再强调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与2010年相比,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债务余额分别增长了61.75%、56.34%和77.34%,快速增长的债务规模和短期集中偿付的压力,无疑让社会各界都捏了把汗。
实际上,2012年下半年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并没有相应减少,不少省市县乡债务率已高于100%。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提出,要“控增量、压存量”地化解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控杠杆也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美国地方政府债务以金融市场为基石,受到《破产法》的硬约束,确保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次贷危机后地方迅速控杠杆。日本长期采取“强管控、精计划”控杠杆思路。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地方政府快速加杠杆,部分地方政府终于在2006年濒临破产,不得已而控杠杆。我国当前地方政府负债率已接近了日本顶峰时期40%的水平,远高于美国。
可以看到,当前的地方政府控杠杆部分借鉴了美国模式。修改后的《预算法》促进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堵歪门、开正道”,对其形成硬约束。但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刚性支出,土地财政终结而地方主体税尚未建立,地方财力捉襟见肘。可预期在未来几年,地方政府仍然非常依赖债务融资,其负债率难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未来几年更可能是走平或略微走高。因此,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的风险也就成为当前一个主要目标。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央政府稳增长重点聚焦于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国务院各部门也不遗余力地落实相关政策。从中长期来看,这三个领域也是中央加杠杆的政策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