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看到学生做题目,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暑假作业来了。这份经久难忘的作业,不是文字,不是算式,而是熟草25公斤。
何谓“熟草”?煮熟的草?当然不是!把青草割下来晒干,那些虽干枯却还透着绿意、散发清香的干草,便是熟草。做什么用?喂牛!
秋风起,白露为霜,草木摇落,牛就没有鲜嫩的青草可啃了。在吃喝这个问题上,牛大概是最好说话的。秋冬季,稻草也好,棒头秆子也好,只要能充饥,牛全认。站着吃,津津有味;卧着磨,慢条斯理。这时令,若能喂一点儿熟草,对牛来说,等于加餐带料,就是美味享受了。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牛的佳肴几经辗转,成了我的作业。25公斤青草是小事,25公斤熟草事儿可不小。得多少公斤青草才能晒成25公斤熟草,我没有概念,反正我真切地领教到这个作业比作文难多了。十一二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挎个柳条筐出门晃了半天,收获却是寥寥。村里大人们看到了就调侃:充军哩!“充军”是吾乡俗语,大概是看戏学来的,描画人在四野里晃荡,形同戏台上林教头那角儿发配远行。当然也有人好心教导:宝宝你手里这小锹子是挑猪菜用的,割草不来事。这倒提醒了我,剐牛草得用镰刀的。镰刀是一尺多长的弯月形快刀,夏收割麦,秋收割稻,那是唰唰的,带劲。我赶紧回家提要求,父亲拿给我一把镰刀头子,就是镰刀用旧了断了半截的那种,还可以用来干点儿小活儿,比如割个韭菜什么的。我有些不中意,就嘟哝。父亲教育:留两个指头挠挠痒,就这个。父亲说得严肃,我一听却乐了。好伙伴三猴子用一种剐草专用的镰刀,结果草没多割,倒把自家的脚割了个豁子。有一次他还把刀弄丢了,这可是做农活少不了的家伙什,要花钱打的。我去喊他一块割草时,经常听到他家里人大声警告:再把镰刀玩丢了,你皮就没得了!我们一听赶紧溜。
说起来是劳动,实际上玩的时间多,干的时间少,勉强盛满篮子,便得胜还朝。望着场院地上稀稀拉拉一把草,大人就笑:晒晒拢拢好,看够不够你自己吃一顿。我辩解:谁让你们把茅草埂子“修”得滑滑滴滴的?我得意自己找到了“作业”效益不高的原因。不光学生在割草,实际全民在割草。本地的牛羊不是放养的,拴在桩上,要喂的;而且,有机肥时代,生产队沤“绿肥”也要青草,每家每户都有任务。所以,草长得再快,也不够割的。苏北里下河地区一马平川,河沟湖荡之外,举凡田地几乎都是粮田。所谓田野,其实都是庄稼地。好在乡村道路原生态,窄窄的土埂杂草丛生,阡陌纵横郁郁青青,不然,我如何才能把我的暑假作业“写在大地上”呢?尽管这样,资源毕竟有限。没有青草,哪来熟草?再说,青草有了,都不一定就有熟草。青草要晒成熟草,得有大太阳。炎夏太阳是大得很,但雨水也多得很。若遇连日阴雨,青草不是变成熟草,而是烂草。“熟草不是一天晒成的”,一放假的时候,大人们就这么提醒过,慢慢地,我领会到什么意思了。
暑假一天天过得好快,我的作业看来得靠外援了。有一天,一个表姐割草归来,遇到我在田埂上“充军”,就把她网包里的青草扒拉一半给我,够我装好多篮子的。这无疑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由得想,有个姐姐真好啊。
更强有力的援手来自我母亲。母亲是做农活的好手,行家一出手,就知功夫有没有。母亲划来一小船,在小河里划了老远,说你看看这河浜上。哦呀,乖乖隆滴咚,这河堤塌塌坡上,狗尾巴草挤挤挨挨,绿油油,肥嘟嘟。一刀一撸就是满满一大把,全不似田埂上匍匐着的爬地藤,精头细爪的。村庄周边抬脚便到的地方,草一长出来就被割了;就是远离村庄的这河浜边上,河堤树荫下那平坦开阔处,也跟我晃悠过的那些田埂一样,早被修理一空,也就河坡下这不便立足的陡壁处,杂草才长得欢。划一小船抵近河浜来割草,真是好办法。舍近跑远,看起来多了辛苦,却也多了收获。母亲不识字,母亲用劳动教会了我劳动。
数年后,已经到城里念书的我读到徐志摩的诗,“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我眼前立马闪现出那青青河边草的画面。河堤上立着高高大大的钻天榆和歪歪扭扭的钉子槐,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照到河浜那些狗尾巴草上,有明有暗,风摇草叶,光影闪烁。一叶扁舟划过清凌凌的河水,满载一船青草的清香。我也想放歌,歌唱那完成作业的欢畅。
我知道,志摩的诗句水灵灵的,而我的劳作汗涔涔的,完全两回事,可我就这么联想了,自然而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熟草25公斤,几多辛劳,我用汗水诠释了诗意。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中学)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02日第4版
作者:陈俊江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全球观焦点:哪些美股适合采
全球观焦点:哪些美股适合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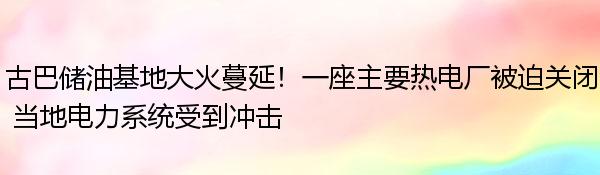 古巴储油基地大火蔓延!一座
古巴储油基地大火蔓延!一座  首届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创新挑
首届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创新挑  天天资讯:俞文正:让百姓喝
天天资讯:俞文正:让百姓喝  ST金正投资者索赔一审胜诉
ST金正投资者索赔一审胜诉  IPO募资235亿元!北交所一年
IPO募资235亿元!北交所一年  玫莉蔻玫瑰明眸紧致凝时眼霜
玫莉蔻玫瑰明眸紧致凝时眼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