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北方的春天已经崭露头角,野鸭子回来了,叼鱼郎也回来了。大地从冰封雪覆中挣脱出来,偶尔会有水墨淋漓的云从天边垂下。也常有混沌的时候。或远或近的尘烟都成为春天最鲜明的意象。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起风的日子,呼兰河南大坝就有三三两两放风筝的人。大金鱼、大乌贼,花花绿绿,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在风中飘荡,天空成了鱼缸、成了海洋;也有放“机器猫”的,大圆脸上几根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几十米长的巨龙,凌空摆动,神采飞扬,放龙的人说,这条龙做了好几个月,成本就千八百块;偶尔也能看见穿戴臃肿浑身雪白的“宇航员”出现在头顶,两三个连在一条线上,脸朝下横在那里,宛如科幻大片。
俗话说“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雨”,如果遇到一个没有风沙的清明,就觉得格外幸运。回祁家窝棚上坟,听不见咿咿呀呀的哭声,往来行人都满脸平和、脚步轻松,好像去赴一场约会。墓地荒草有的已被烧光,黑乎乎一片,细小的新绿试探着,从这里钻出来,从那里钻出来,鲜明耀眼。正月十五送的灯还在,横七竖八躺在风里。
《淮南子》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亦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节气是天时,节日是人时,天朗气清、慎终追远,故清明兼有自然和人文两种内涵。
在清明与谷雨之间,乡村要完成一系列农事,搂地、烧荒、翻地、播种……春和景明,吐故纳新,一切都从头开始。此时,从严冬走来的人们,走到天地间,追念故人、亲近自然。
母亲刚去世那些年,每逢清明,姥姥就从十几里外的高家屯走来,只要一看见祁家窝棚树梢,就大放悲声,一直哭到坟地、哭到我家。好在姥姥心胸宽广,哭过就好,该吃吃、该喝喝,活到90多岁。
清明上坟哭哭啼啼的还有奶奶。小时候与她一起回娘家,去田间给外曾祖父、外曾祖母上坟。青烟升起,奶奶和两个姨奶突然呜咽起来,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诉说,哭到伤心处就坐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悲凉哀转之声有时拖得很长,旁边枯草也被她们揪了一把,似乎只有青烟缭绕中的悲悲切切才能完成对父母最彻底的思念。
我远远站着,哭声让我害怕。哭了一阵,有人戛然而止,互相劝慰几句,搀扶着起来,这场清明的泪雨便宣告结束。然后踏上来路,依旧是满嘴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这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儿时清明,爷爷曾让我用一截短木在黄纸上砸。不知木棒用了多久,也不知从哪辈人流传下来,已经沧桑成酱色,光滑发亮。木棒一端凿成铜钱模样,外圆内方,中间是凹进去的浅槽。印纸钱时,我跪在灶前,从灶坑里抓把灰,黄纸平铺其上,我便一手握木棒,一手举锤,一排排砸下去,黄纸就有了深深浅浅的印儿。砸完折叠,一张张抽出捆成一沓,清明的纸钱就做好了。如果给远方先人送纸钱,黄纸上还要写地址姓名,就像写信一样。
如今清明,回祁家窝棚上坟,每次都要到村中叔叔或姑姑家吃饭。家里常包的是酸菜馅饺子——经冬的酸菜尚新鲜,清清白白,不需要剁得太细,简单洗过后挤去汁水,酸菜裹挟回转的阳气,与年前的笨猪肉搅在一起。新包的饺子挺拔整齐,菜的酸香与肉的肥厚交融,让人不忍放下筷子。
在繁忙的间隙,在新的轮回肇始之处,长幼围坐唠些家常,春的薄凉和死的苍茫都在缭绕的人间烟火中远去,取而代之是生的气息和家的温情,这种感觉真好。
(作者单位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实验学校)
《中国教师报》2023年04月05日第16版
作者:张 猛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特斯拉低价车要来?或定价10
特斯拉低价车要来?或定价10  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
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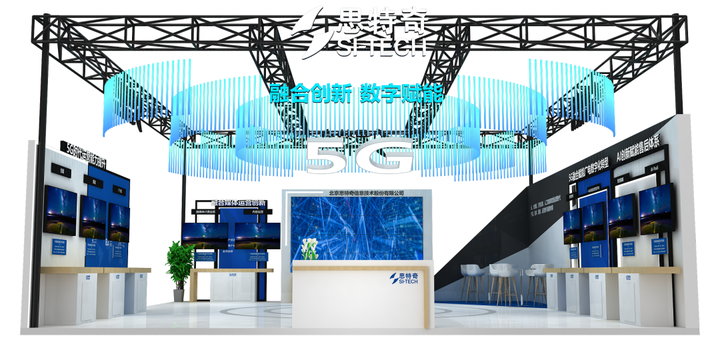 融合创新 数字赋能 | 思
融合创新 数字赋能 | 思  全球观察:锂价大溃退,宁德
全球观察:锂价大溃退,宁德  “AI四小龙”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龙”上市之路各不相  超给力职业指导——巴斯大学
超给力职业指导——巴斯大学  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