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昊骞
 【资料图】
【资料图】
日本WOWOW卫视,2021年10月宣布将翻拍漫画家今井大辅的作品《擅入寄居者》,引发了人们对无家可归的“水蛭”人群的关注。水蛭不仅是流浪汉,而且会复制主人家的钥匙,摸清主人的生活规律后寄居其中。他们是游走于都市边缘的无身份者,是生活在钢铁丛林中的动物。
展现他们的生活,或以他们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已经有许多,除了《擅入寄居者》以外,还有法国小说家埃里克·法伊的作品《长崎》、韩国悬疑电影《寄生虫》等。尽管水蛭与任何人类群体一样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是脆弱、孤独与危险总是绕不过去的三个关键词。寄居者事件不仅是饭后的谈资,同时也蕴含着窥探与反思社会的一个侧面的资源。
水蛭成长史
《擅入寄居者》是日本漫画家今井大辅的作品,原作连载于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故事的女主角是21岁的佐仓叶子,刚刚成为一名“水蛭”两个月时间。在漫画中,“水蛭”这个词第一次出场是写在叶子的胳膊上:“你也是HIRU吗,佐仓”。HIRU用假名写作ヒル,是水蛭的意思。
《长崎:看不见的寄居者》
当时的佐仓还一脸疑惑,不知这个词语代表什么意思,更不清楚怎么会有人在陌生的城市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此处细节展现了整部作品的主线:水蛭成长史,或者说,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从女儿—学生—公民转向了无名的漂泊寄居者。
她成为水蛭的基本动因来自家庭环境,她成长于一个刻板印象化的传统父权制家庭。父亲专横而冷血,用叶子自己的话说就是“魔王”,不仅动辄殴打叶子,还会说出让她工作后还清养育费用的话语。她的水蛭之道的起点,正是再一次遭到父亲的暴力对待。
佐仓的母亲懦弱隐忍,整日只是以泪洗面;弟弟则已经完全适应了畸形的家庭环境,通过讨好父亲的方式来换取赞赏和安全。终于做好离家出走的决定后,佐仓本来约好和男友一起坐夜班大巴,不小心睡过了头,只好徒步回男友家,给他收拾了家务,做了晚餐,却正好撞见男友劈腿的现场。等到男友走后,她打开电视,看到新闻中说她没赶上的那一班大巴发生车祸,全员丧生,而由于她把身份证件落在了车上,所以被认定为死者。
已经社会性死亡的她,只觉得这是“一出喜剧”,于是毅然去了另一座距家乡五小时车程的城市。一只青涩的水蛭就这样诞生了。
她的前两个月还算顺利。日本人有在玄关放置备用钥匙的习惯,于是佐仓就守在公寓楼外面,看到有人出来便尾随而入,查找观察屋主的身份和家庭环境,如果合适便配一把钥匙,将其开发为自己的备用屋之一。公务员、白领等作息规律的上班族,是她最喜欢的猎物。通过这种方式,她已经占有了七间屋子,足够轮流安排自己一天的生活。
相比于公园和地铁里的流浪汉,她有好多处遮风挡雨的处所;相比于收容所里的人,她不必受到监狱般的全天候管制,拥有限定条件下的消极自由。从表面来看,除了两个多月都没跟人说话的孤独,还有要随时警惕主人早归的风险以外,她似乎已经经营起了自己的寄居小日子。
用当初在她胳膊上写下HIRU的水蛭同道和前同学月沼诚的话说:“游走于屋主不在的房子,靠别人的东西生活……现在的你佐仓就是水蛭。”同时,月沼也向她发出了警告:“再这么下去会被杀掉哦……也没有人会保护你。”
果然,佐仓很快就陷入了一连串生死险境。与月沼初次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她就被另一只“水蛭”引诱到一所学校中,险些丧命,多亏了月沼出场才救了她,还割下了意欲杀害佐仓者的一只耳朵。目睹这样的场景,给佐仓造成了重大冲击,让她萌生了回家的念头。这或许是她最接近回归社会的一次机会。
她从窗外看到家人在餐桌旁吃饭,家养的小猫阿纯向她扑来,她的房间也保留着原样,似乎家人还在期盼着她的归来。她不禁在想,“父亲会像这样,变成一个单纯的偏执老爷爷吗……”但即使在她自以为安全的家,水蛭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一只躲在她身后的水蛭,将听到声响后前来查看的佐仓爸爸绑了起来。不过,佐仓此时已经有了身为水蛭的觉悟,用刀片赶走了对方,随后回到了水蛭的生活轨道中。
为了顺应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佐仓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不顾公序良俗的危险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月沼逐步建立了类似于少年漫画中常见的伙伴情谊。从第1册中依赖月沼才活了下来,并学到了水蛭亚文化的潜规则,到第5册的末尾中说出“月沼由我来守护”,佐仓走出了蜕变的冲击与阵痛,建立了之前求学工作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坚定身份认同与支持网络。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擅入寄居者》中大量描绘了脱离社会规制与庇护的丛林生活,但一直有一条暗线:水蛭世界是一个有规矩、有情义的江湖。尤其是相比于佐仓原本的所谓正常社会关系,月沼与她的患难之交反而要真挚深厚得多。
因此,对佐仓来说,水蛭生活一方面是被抛入后的消极习惯过程,但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她能够主动改造自己,形成有意义的新世界观。除了与月沼的情谊外,还有一件事能体现这一点。她主动找一位警官蹭饭,还偷走了他的钥匙,进入了他的公寓。
更讽刺的是,警官钥匙链上有一位手持十手的“同心”卡通形象。同心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1603年—1867年)负责城市治安工作的下级官职,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警察,招牌武器是适合擒拿罪犯的“十手”,形似中国古代捕快所用的铁尺。怀疑佐仓是水蛭的警官跟踪她时,正好看见她在警官公寓楼下丢下他的钥匙链。此事坐实了警官的猜测,也表明了她对警官代表的法治社会的弃绝。
日剧 《擅入寄居者》剧照
如果说《擅入寄居者》展现了一幅浪漫化的寄居者冒险画卷,凸显了人类固有的脆弱性和公民社会下的暴力危险,根据法国小说家埃里克·法伊中篇小说《长崎》改编的图像小说《长崎:看不见的寄居者》,则是一首表面平静得多的叙事诗,但同时又像一根从头紧绷到尾的弦,从来未曾得到真正的释放。
在壁橱里住了一年的女人
《长崎》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中篇小说,曾荣获2010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小说开头就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没有发生在长崎,但是发生在日本。这则社会新闻曾被多家日本报刊报道,包括2008年5月的《朝日新闻》。”后来,法国自由画师阿涅丝·奥斯塔什根据这部作品创作了图像小说《长崎:看不见的寄居者》。
寄居者是一类真实的社会现象。2020年,29岁的日本职业摔角解说员樱田爱实发现了奇怪的迹象,比如电费猛增,回家后发现原本插在墙上的遥控器跑到了地上,浴室地面的奇怪脚印。后来警方在浴室天花板上发现了食品包装袋,这意味着之前应该有人由这里出入公寓。另外,美国也报道过众多此类案件,寄居时长从两天到半年不等,有时是纯粹的陌生人,也有屋主的前男友等熟人。
与动辄见到血光的《擅入寄居者》相反,《长崎:看不见的寄居者》中不曾有过一次暴力场面,甚至连争执都没有。屋主是一名年过五旬的独居中年男子,在气象局工作。在怀疑有人侵入后,他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从此每天上班时就经常查看家中的动态。几天后,他终于看到了寄居者,随即报了警。
他是事后到警局做笔录时才知道寄居者的情况,两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是在三个月后的法庭上,但两个人也没有过一句对话。他从未提到她的名字,只是用“被告人”或“寄居在我家的女人”代指,而她也没有当庭道歉,只是出狱后才写了一封信,委托房屋中介转交给已经搬走的屋主。全书完。
在平淡如水的表层背后,我们得以窥见寄居者群体的内心及其映射的社会状况。屋主名叫志村公房,56岁,工作是预测长崎附近海域的天气情况,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这也是引来寄居者的重要原因。他产生疑心的起点是冰箱里的一盒果汁:他在盒子里放了一把尺子,上班前还有15厘米,但回家后只剩下了8厘米!
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他决定在家中的每一个房间都安上摄像头,“远距离地盯住我志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便当’”。便当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几十年来,他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走入玄关,进入厨房格,吃饭,进入浴室格,洗澡,进入卧室格,睡觉。他清楚地记得冰箱里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也记得桌子上摆件的位置和朝向。谨慎规律的生活既让他多次发现“失窃”端倪后成功捉到寄居者,也为寄居者提供了赖在客卧壁橱中长达一年的条件。
客卧上一次有人住,是一年前志村的妹妹和妹夫来的时候。从那以后,他连来家里坐一坐的访客都很少有。下班后,他从来不和同事们去居酒屋社交,家里更没有太太做好饭,打开门迎接自己。他偶尔在睡梦中“无意识开始喷发”,幻想出浮世绘般的绮丽场景,只是他本人依然面无表情,哪怕自己正骑在一条身穿和服的东洋美人鱼身上。
寄居者是一位无名氏,我们只知道她的姓氏和志村一样“平庸之极”。相比于一进屋子就乱丢鞋子,大剌剌地躺到主人的床上,又是洗澡,又是做饭的佐仓,58岁的无名寄居者要小心得多。她是一名长期失业的女人,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勤杂工,失业后就靠救济金生活。等救济金也被停掉后,她立即退掉了租住的房屋,离开原来的街区,来到没有人认识自己的新环境中开始新生活。
她会像志村一样记住冰箱和餐桌的模样,尽量不动屋主的食物,而是靠翻便利店后门垃圾箱里扔掉的食物为生。她发现,这些食物“只是刚刚过期而已”。直到住了几个月后,到了下大雨没法出门的时候,她才会从冰箱里拿一些蔬菜水果来吃。可惜,她最后在客卧壁橱的角落里被警察发现了,像“一只吓呆了的小兽,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在水粉画的笔触和琐碎日常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去罪化的寄居者图景。寄居者并不觉得自己犯了罪,只是觉得:“我的错,唯一的错,就是去了我并没有权利置身于其中的地方。”
志村自始至终没有对寄居者的仇恨,折磨着他的是“我无法再感到那是在我自己家里”的感受。他在法庭上没有痛斥或控诉,而只是默默地给自己住了几十年的“便当”挂上了待售的牌子。就连警察和法官都仿佛觉得这是一起令人厌烦的案件,只想尽快了结,免得耽误了其他更重要的事。警察向志村介绍案情时的语调“像天气预报一样”,法官则给寄居者判了最低限度的刑期,扣除掉羁押的四个月,她只服刑一个月就获释了。
排除了犯罪与正义的耀眼光环后,我们看到了都市中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意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提出的概念,就是指被剥夺了全部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纯粹生物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水蛭”和“小兽”都是赤裸生命。
只是《长崎》中的“小兽”被剥夺得更加彻底。她之所以搬离原来的街区,既是因为无钱续租,也是因为没有脸再面对哪怕只是偶尔能在街上遇到的邻居了。于是,她主动选择了更加彻底的隐居和窃居生活。这种生活所能承载的全部社会关系,不过是与屋主的默契和对屋子本身的眷恋。她没有结识新的朋友,没有遭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危险,更不要说暴力了。但正如她在出狱后写给志村的信中所说:“在我这把年纪,不会再有什么职位还在等着我。……意义并不存在。意义的概念是由人发明的,是为了让一只手掌抚平心中的忧虑。”
韩国电影《寄生虫》剧照
信的末尾,揭示了无名寄居者过往生活的一角。她从小沦为孤儿,参加过1970年代的反政府活动,被捕后改名换姓,却始终无法融入社会。但这些褪色的宏大叙事碎片并没有将故事拔高,甚至并没有让故事更加合理,因为志村与她有着许多平行的念头。
第一次与年轻同事喝酒后,他的想法是“我这颗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躺在床上,他只觉得:“这生存的匮乏与艰辛昭然若揭。没有任何抱负从中生出,也没有任何希望。这个女人真该遭诅咒。由于她,浓雾消散了。”如果说他仇恨过她,那不是因为她侵占了他的财产或权利,而是因为她让他想到自己在一年时间里随时可能被捅死,让他意识到自己家里唯一长住过的女人是一个看不见的寄居者。
简言之,她逼迫他直视自身,并得出了惨淡的结论。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共同处境的共情吧,只是这种共情的表现形式不是热烈的同志情谊,而是冷漠的不屑。
彻底的VUCA生活
寄居者的生活是不稳定的,是孤独的,可以说是彻底的VUCA生活。VUCA是易变(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和模糊(ambiguity)的缩写。它最早是美国陆军学院提出的,本意是描述冷战结束后的多边世界局势,后来延伸到了企业、组织、个体乃至社会总体状况上。
寄居生活往往既是生活压迫下的应激反应,也是一种带有觉醒意义的主动选择。月沼诚曾说过:“所谓的‘社会’就是纸盒文字,将这些东西舍弃,就代表着得回到野外。”在《擅入寄居者》的语境中,这样的反思代表着血的教训。对寄居者来说,不被警察和法律代表的社会秩序所清除就已经是万幸,更不能奢望除了自身和极少数“伙伴”以外的任何支持。月沼诚点明了寄居者VUCA生活的另一面:危险。
危险是双向的。一个方向是社会对寄居者的系统性排斥。在大多数情况下,寄居生活并不构成人身侵害,甚至造成不了多大的财产损失。《长崎》里的无名寄居者喝掉了7厘米的果汁和几盒酸奶,吃过一条鱼,洗澡时消耗了一些自来水,洗完后还会把浴室清理一番,免得被发现。用她自己的话说,“他志村与我和平共处,恰如人们与一只老鼠共居一段时光:出于好奇或者出于怜悯。”
《擅入寄居者》中的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寄居者之间,或者是为了抢夺其实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地盘,或者是寄居者群体之外的某个人雇凶杀人。换句话说,与黑帮的逻辑相差不大。
寄居生活更算不上是任何意义上的反抗,正如躺平不算对996的反抗一样。但尽管如此,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是不会主动容忍任何寄居者的。逮捕,出庭,入狱,回归同样乃至更加彻底的VUCA生活,这就是寄居者与社会所能发生的一切关联。在人们没有把橱柜打开之前,小老鼠们可以躲在里面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寄居者对被寄居者同样可能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可能是潜在的,比如志村躺在床上的一阵阵后怕,但也可能是现实的,比如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虫》中末尾的杀戮派对。影片的前半段讲述了穷困潦倒的金家父母兄妹四人混入富豪朴社长家,顺利过上寄居生活的奇遇。可随着被金家人排挤出去的前管家突然折返,一家四口陷入了被告发的危险之中。凭借人多势众,金家人最终制服了管家和同样藏在豪宅地下、寄居躲债的管家丈夫。目睹妻子被害后,失去理智的管家丈夫捅死了金家妹妹,随后被金家爸爸反杀。这时,目睹着庭院里欢腾的朴家公子的生日派对,又想起朴社长嫌弃自己有“坐地铁的人身上的味道”,又将朴社长杀害。
寄居者的本意并不是成为罪犯。相反,他们只是想享受一把富人的生活。金家兄妹先后成为朴家小女儿的补习教师,金家爸爸当上了司机,最后把金家妈妈塞进来做新管家。趁着朴社长夫妇出门的契机,一家四口可以在客厅里狂欢一把,再赶在主人回来之前打扫好房间——这便是他们天大的奢望。只是在暴露的风险和主人无意的侮辱言语促发下,狂欢节才变成了修罗场。
与其他背负着危险、犯罪、能力低下、不讲道德等刻板印象的弱势群体,如穷人、流浪汉、少数族裔一样,寄居者也是非人化修辞的对象。《擅入寄居者》贯穿全篇的“水蛭”一词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事实上,“擅入寄居者”是引进方起的中文名,日文原名就是ヒル,即水蛭。
相比于人类除之而后快的害虫水蛭,《长崎》中的“小兽”与“老鼠”比喻强调的是寄居者在“真正的人”,包括屋主、警察、法官及其代表的社会“大我”面前的无力。《寄生虫》中多次提到的“蟑螂”又多了一层含义:寄居者,或者穷人虽然不能对富人造成什么伤害,但一想到或者一看到他们,还是会令富人一阵厌烦。当然,从影片的结局来看,这种看法显然是失算的。
寄居者不仅仅是社会新闻或花边谈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处于VUCA境遇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风险呈指数增长,规避风险的机会在消失……假如一切都成了危险,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什么是危险的了。假如无路可逃,人们最终也就不必再庸人自扰。风险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回移动。”
作为彻底的放弃者,寄居者或许正是普遍风险社会的投影或逻辑结论。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每日简讯:港股低开,恒生科
每日简讯:港股低开,恒生科  全力以赴稳住基本盘 外贸高
全力以赴稳住基本盘 外贸高  “大筒仓”元宇宙空间项目特
“大筒仓”元宇宙空间项目特  每日热议!天津LNG二期储罐项
每日热议!天津LNG二期储罐项  “猪王”牧原股份涉嫌虚增利
“猪王”牧原股份涉嫌虚增利  围绕绿氢供应疏通产业链堵点
围绕绿氢供应疏通产业链堵点  中国田间日丨藏粮于技 潍柴
中国田间日丨藏粮于技 潍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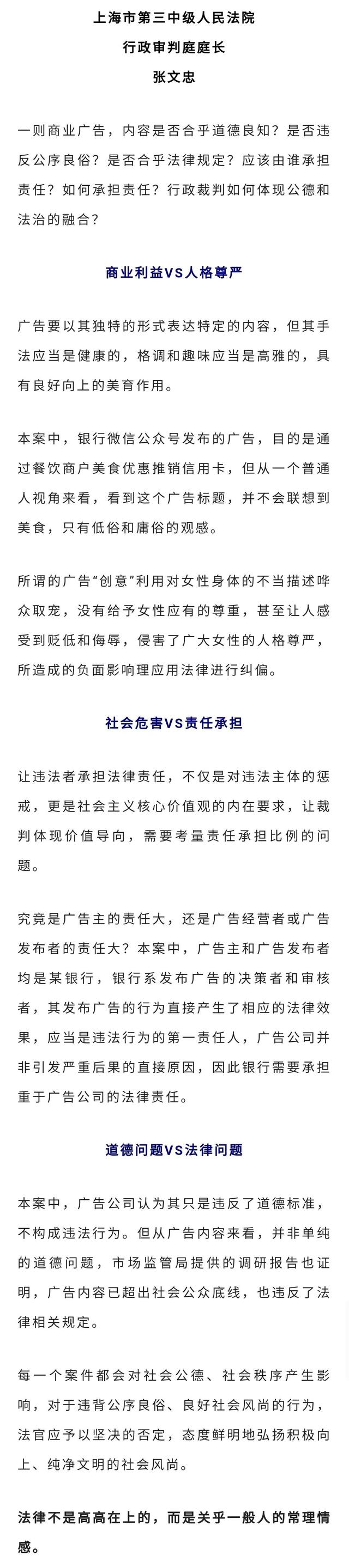 发布贬损女性广告被罚90万!
发布贬损女性广告被罚90万! 



